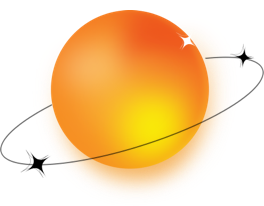被OpenAI估值30亿美元收购,Windsurf CEO亲述创业“断舍离”生存法则
图片来源:20VC
Z Highlights
敢于自我颠覆的公司能最早抓住新范式。初创公司成功不是因为做对很多事,而是因为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好。每次转型之后做到“断舍离”,让整个组织完全投入到新方向中能大大提高成功概率,最终的成功足以覆盖其他所有失败成本。
留给初创公司最大的机会在于,构建需要非常高密度工程直觉的东西。开发者工具真正的壁垒在连续一整天、整个工作流中的体验,只有做过一线开发、对用户有高度同理心的团队才能做出来。大公司往往受到组织结构限制难以做到极致。
未来最成功的AI工具,一定是那些能动态调整人机边界的系统。用户并不是一直希望“全自动”或者“全手动”,而是希望在不同场景中,有不同层级的控制。Agent的判断力比模型本身的输出质量更难构建,但也更有价值。
Varun Mohan,初创公司Windsurf的联合创始人兼CEO。Windsurf专注于构建面向工程师的 code Agent系统,因被收购成为迄今AI领域规模最大的收购案之一而广受关注。本次访谈发布于2025年6月,由「20VC」节目的创始人Harry Stebbings主持,围绕AI产品构建、初创公司战略转型、Agent与IDE的融合趋势等核心议题展开。
初创公司战略:选择大于努力
Harry:Varun,我真的非常期待这次对话。我从Lee Marie、Neil Mehta和很多其他人那里都听到过关于你的好评。特别感谢你今天能来。
Varun:谢谢你邀请我,Harry。
Harry:你曾经说过,真正正确的想法几乎从不会在最初就出现。我想从这个话题开始问你:你后来是怎么重新理解“一个真正优秀的创意”到底是什么的?
Varun:Peter Thiel的那套理论还是有不少道理的,比如说创业一开始要选择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向。但问题在于,大多数“不显而易见”的想法其实本身就是坏主意。你走了一条非传统路线,并不等于你选的就是一个好主意,这一点很多人经常会忽略。
从更高的层面来说,如果你选择的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方向,那几乎可以肯定,这里面就没有什么“alpha”优势了。大公司会比你先一步入场,因为它们有更多的渠道资源和资金。
所以,初创公司通常要靠选择那些在大众看来“不太寻常”的方向来胜出。但同时,你也必须有足够的自知之明,明白你的那个“特别”的想法很可能其实并不是好想法。
从失败到突破:战略转型与快速成长
Harry:你们当时转向Windsurf时,你自己认为最“非典型”的认知或者见解是什么?
Varun: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做过一次转型。的第一版产品,连公司名字都已经换过两次了。最开始叫 Exafunction,当时在做GPU虚拟化技术,背后的逻辑是:未来的计算负载会越来越依赖GPU。这就是最初的使命。团队里很多人此前都在自动驾驶、AR/VR这些领域干过,当时团队还挺小的。
事实证明,我们在一个方向上是对的——GPU确实会变得越来越重要,我们判断NVIDIA会卖出大量GPU,这点没错。但错的是:低估了GPU工作负载的集中程度。我们以为市场上会涌现出很多不同结构的模型架构。但最后出现的情况是——几乎所有架构最终都趋同成了Transformer。在这样的技术格局下,作为基础设施提供方,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化优势可言。所以当时必须转型。但这就是市场的现实——有些东西在入局前你是很难知道的。最初的假设错了,因此只能放弃。有时候你会有一个“很特别”的视角,但市场走向可能完全不是你设想的那样。
Harry:完全认同。但问题是,很多人太执着于自己的“论断”。这也是我不太喜欢所谓“投资论断驱动型”投资人的原因之一。很多创业者都深深迷恋自己的想法,而他们从小到大听到的也是:真正能坚持到底、有韧性的创业者,才是最终胜出的人。但你在之前提到,“不要对自己的想法太上头”这点我很赞同。你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张力?一边是坚定执念,另一边是理性抽离。
Varun:这其实是创业最难的部分之一。你必须同时在脑中持有两种看似矛盾的信念:一是非理性的乐观主义,如果你一点乐观都没有,那你可能连床都不愿意起,更别说创业了;二是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。你每天都得问自己一个问题:“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?”如果答案是“不太清楚”,那你必须立刻改变方向,尽快带着整个公司转向。在创业领域有件很荒谬的事是:你不会因为坚持做错事而得到任何认可。或许你可以告诉同事、投资人或朋友说:“我还在做这件事。”但当你失败时,没有人会在意你坚持了多久。
Harry:那在今天这个阶段,你觉得自己现在还对哪一个想法“爱得太深”了?我可以举个例子:作为投资人,我自己非常痴迷于“投资组合构建的纪律性”。我喜欢那种通过精心组合来控制风险和机会的投资方式。但现实是,在当下这个时代,你必须打破很多规则。虽然我并不是在鼓吹盲目冒险,但的确需要比传统模式更具弹性。这就是我放不下的东西。那么你呢?
Varun:如果从经验主义角度讲,我们过去确实每一次都对自己的想法太过执着了。站在外面看,可能有人会觉得:“你们公司能多次转型,这是个积极信号。”但我自己其实一直在反思,为什么不能更早地做出转型?
比如说,从GPU虚拟化转型到做code AI产品,我现在都还会自责:明明早就看到了信号,却还是拖了三个月才下决心。当时合作的公司,大多数都是做自动驾驶的,正值“ZERP 时代”(零利率时代)最热。但到了2022年中,很多这类公司都无法继续融资,我们才开始意识到,市场在变,技术也在变,而我们的潜在客户似乎也撑不了太久了。我现在回头看,真希望早三个月动手。
Windsurf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。我们早就知道Agent会非常强大,其实完全可以更早开始做Windsurf。
Harry:我最近采访了Fiverr的CEO,他说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——“time to clone”(被复制的时间)大幅缩短了。也就是说,一家新公司推出一项创新后,别人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东西。那么我想请教你,在这种情况下,“第一个做到”这件事到底还有多重要?
Varun:抢先一步主要带来两个作用。第一,它反映了你这家公司本身的运作方式;第二,它让你可以更快地从市场中学习。
让我先讲第一个。通常那些能率先进入新范式的公司,都是愿意自我颠覆的公司。他们的组织结构对变革非常开放,能快速在转弯处掉头。他们不断投资于非渐进式的技术,愿意打破原有的自我结构。这种特质对软件或code AI这样的快速变化行业来说尤为关键。
第二个方面是:抢先一步意味着你更早进入市场,可以更快地学习,这也使你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迭代的领导者。你会最早看到这个领域“尸体堆在哪里”——也就是说,你能率先看清哪些方向死得最快、哪些坑你踩过了、哪些方向值得坚持。
我自己特别喜欢想一个问题:如果我们能把产品更早地推向市场,在第一个月里,就能从用户那里学到什么?这些知识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快构建下一个版本?我相信,这种“学习优势”可以随着时间持续产生复利效应。
Harry:但换个角度看,看到别人先试错,不也挺好吗?你能观察他们哪里做错了,然后吸取教训,自己出手时就能避开那些坑,节省大量试错成本。
Varun:在软件领域问题在于:很多错误其实都发生在公司内部的研发环节,而外人是看不到的。公司内部现在有一种积累下来的“品类直觉”:有些想法连碰都不会碰,因为我们曾亲自尝试过,发现根本行不通。这种“失败的记忆”已经写入了公司基因。我们现在的创新,其实很多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试错的基础之上的。而这些东西,是你从外部观察一家公司的时候很难看出来的。
Harry:你们以前做过什么尝试,后来发现行不通,但外界并不知道的?
Varun:我们确实发布过这个产品的测试版,而且内部自用(dogfooding)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可以举几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,去年推出过一个code review的测试版产品。当时试过很多种方式来交付这个code review产品。做过一个Chrome浏览器扩展、还在公司内部做过一个并行的网页版工具......在内部试了各种方案,但都感觉不够理想。而在几周前,最终发布了现在这个code review产品,它体验好得多,也真正提供了很高的价值。之所以以现在的方式发布,是因为吸取了去年所有失败尝试的教训。
我再举一个例子,是关于随Windsurf一起发布的code Agent产品。我们在去年年初就做过第一版,但那个版本的效果并不好。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。也正是因为那次失败,我们才得以回到最初的设计阶段,逐个修复那些关键要素,为最终发布Windsurf做好准备。其中包括:需要在code-based understanding上做到足够好,同时底层模型本身也必须变得更强。当模型的性能提升上来了,内部在code-based understanding上的研发也成熟了,这时候才真正准备好发布这个产品。所以这就是那种情况——如果只是等着别人把这个产品做出来,我们最终就得在多个维度上去追赶他们,才能把产品推出来。
Harry:你会建议创业者在早期尽可能多地融资吗?毕竟这本质上就是你能拥有的“试错次数”,实验的次数。如果你融得多,就能多试几次。基于你的经验,你会建议这么做吗?
Varun: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,稍微透露一下吧:我们在还在做GPU虚拟化项目的时候就完成了A轮融资,当时是Green Oaks主导的。
Harry:他们也是你的种子轮投资方?
Varun:是的,他们也投了我们的种子轮。至于他们是否应该在A轮继续投,我就留给观众自己判断了。但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心——哪怕转型了,我们依然有足够的资金去探索新的方向。
当时我们发布了Codium这个扩展产品,完全是免费开放的。之所以敢这么做,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强大的技术积累,另一方面是公司账上还有足够的现金支持我们推出产品,不必在意短期收益上的细节。所以我认同你的观点,资金确实意味着你能尝试的次数更多。但前提是这家公司必须具备快速转向的能力。很多公司到了十人、十五人、二十人的阶段之后,就不再愿意完全推翻原有方向。但我们不一样。我和我的联合创始人是在一个周末决定要做Codium的,到了周一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整个团队。那一天起,所有人都转去做Codium,尽管当时原来的业务已经有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了。
Harry:那有没有什么结构性的做法,能帮助一个公司在转型后迅速反应、快速落地?
Varun:我一直坚信,在初创公司里,成功并不是因为你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,而是因为你把某一件事做得非常好。就像我之前说的,要拥有一个真正好的点子,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设想一下,有两家公司,每家都在做不同的产品,而每个产品的增长都是按指数曲线变化的,会有一个所谓的“R 值”。那作为初创公司,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全力聚焦那个R值更高的产品。同时投入到两个产品中是完全不合理的,尤其当它们的增长曲线不在同一个数量级时。
所以每次转型之后,正确的做法就是果断放弃旧的方向。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件事,很可能对接下来的新业务根本没有任何战略相关性——它的营收倍数、增长潜力都和新业务没法比。如果你能做到“断舍离”,让整个组织完全投入到新方向中,你的成功概率会大大提高。但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决定。你需要去告诉团队、投资人、客户:我们不会再继续做原来的那一套了。但一旦你下定决心了,其实执行起来会轻松很多。
Harry:当你已经在做几百万美元营收的时候,放弃原有业务等于自己吃掉自己的收入,这真的很难。所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。你刚才说,成功其实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,而要做到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够难了。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其实很想去做的事,只是因为你们坚持专注,所以暂时没法做?
Varun:在我们所在的领域,注意到一个趋势:Windsurf的很多用户并不是专业程序员,而是那种“感受型编码”的用户,他们用Windsurf的工具在构建真正有用的应用。比如公司内部就有一位不是工程师的同事,他是负责合作伙伴关系的,他用Windsurf的产品自己搭建了一些应用,替代了过去内部采购的一些销售工具,总共节省了大约50万美元的开支。
Harry:所以他写代码帮你们节省了50万美元?
Varun:对,他自己搭建了公司内部用的系统,比如合作伙伴门户、报价工具等等。这些原本都是每年要花几十万美元购买的销售类SaaS工具。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现象——这些工具本身都很定制化,以前公司不会自己去开发这些内部工具。但现在,软件的开发成本大幅下降,尤其是那些“临时性”或者“轻量级”的软件变得极易构建,于是非技术人员也可以自己搭建出功能完备的应用。所以在Windsurf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:怎么让这类用户的生产效率变得更高?
但这中间始终存在一个张力——如果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提升这类“非工程师用户”的体验上,那可能就会牺牲掉对真正开发者、尤其是处理大型代码库的工程师所能提供的深度支持。这终归还是一个聚焦与取舍的问题。
Harry:Windsurf的使命到底是要让工程师效率提升10倍,还是让普通人也能像工程师一样工作?
Varun:目前的重心是前者,也就是让专业工程师变得更高效。而后一种结果,是专注做好前者之后的自然衍生。因为底层的技术能力是具备的,它确实能够赋能非技术用户。但产品重点明确是放在如何提升开发者的生产力上。
Harry:那将来你们和Cursor会不会趋同?你们会逐步扩展到“可爱型工具”(lovables)和“低阶组件”(bolts)那一类用户?而那些工具也会反过来尝试走向你们所在的专业开发者方向?
Varun:这确实是我们常常被问到的问题。那些专注于“非开发者”用户的工具,比如lovables、bolts类产品,随着时间推移,确实会不断往更深的方向发展,加入越来越多的调节项、配置能力,提升可定制性。而对我们来说,如果能够真正深入理解代码,尤其是大型代码库,那么自然就能让非技术人员也构建出应用,且无需太多额外工作。
不过我想说的是,如果现在就去针对非技术用户构建产品,那就等于放弃了在帮助专业开发者方面所能做到的深度。所以我相信,最终这两个方向确实会趋同:一个真正理解你代码库的公司,最终可以只通过极少量的自然语言指令,就构建出一个和你现有代码逻辑一致的完整应用。
Harry:如果你现在有无限资源,有什么是你会用不同方式来做的吗?
Varun:我想我们会在公司内部尝试更多的项目,会做更多“下注”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,现在公司内部尝试的产品方向中,大概有50%或更多其实是失败的。我们有大量的产品和技术研发是在为未来做准备,其中的大部分,最终都会失败。
但这也正是初创公司的一大特征:那个最终成功的方向,足以覆盖掉其他所有失败带来的成本。如果资源无限,我会让我们失败得更多——因为真正起作用的那个点,足以带来颠覆性的收益。
Harry:我之前和Neil Mehta聊过一些关于你的事,他说我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——你是怎么做产品的?你们的产品开发节奏是什么样的?你刚才提到内部项目失败率很高,那在你看来,有哪些不那么常规的产品构建方式,是你特别重视的?
Varun:外界有一种“常识”,认为一家工程师数量越多的公司,产品就做得越好。但这种看法有点把软件研发简化成了流水线工厂的逻辑。我真正认同的方式是:当一个想法还没验证、方向还不明确时,反而应该让非常少的人来负责它。
如果你把十个人投入到一个尚未被证明是否成立的项目里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,而在没有结果之前,这些意见都不能算错。这时候就很难达成一致,也很难让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推进,还可能会造成沟通混乱。更有效的方式是,找一小撮非常有主见的人,让他们去快速验证一个想法是否成立。
接下来问题就是:一旦你有了一个雏形,怎么判断是否应该继续投入?这个判断其实很难。不过公司有个经验教训,很多人之前在“硬科技”公司干过,比如做自动驾驶的。我们总结出一个经验是:当你真正有了一个好想法时,就算是初始版本、粗糙版本,也已经能体现出惊人的价值。
比如最早构建Windsurf里的Agent时,就算那个版本还很粗糙,它已经能做到很多过去八九个月以来我们从未实现过的事情。那一刻我们就知道:这个方向有潜力。当你确定了这个粗糙版本已经“有生命力”,那就是时候追加资源,把它推到更深的层面。
Harry:难怪Neil那么喜欢你。他常跟我聊“用户震撼体验”——就是那种第一次接触Agent的时候,被它的能力惊到的瞬间。我想深入问几个细节。你刚才说一开始只是“少数几个人”在做这些新项目,那具体是多少人?你在公司内部怎么组织这种“新方向”的项目团队?
Varun:大概就是三四个人左右。
Harry:那是几个工程师加一个设计师吗?
Varun:对,其实如果项目本身是纯粹的系统技术,可能就只是几位工程师在做。我们做的是开发者工具型产品,这有个优势: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本身就是目标用户,他们在用 V0版本的过程中就会形成直觉,判断一个“粗糙但可用”的版本是否有潜力。
Harry:那预算和开发时间呢?是你设定的吗?还是由团队成员自己决定?
Varun:我们其实没太考虑过这件事。这部分可能是因为现在身处的是一个“非受限市场”——也就是说,如果你能开发出一项能加速软件开发的优秀技术,对客户的价值是巨大的。所以基本不会从“这个项目的预算是多少”的角度去评估事情。
但内部确实会关注一点:这个项目的进展如何?我们有没有在不断解锁新的进展?要不要决定把它搁置,去做别的?这不是一个民主决策过程,更多是公司内部的自上而下的判断。
Harry:有没有那种你们曾经搁置过、但事后回想其实应该坚持做下去的项目?
Varun:我们最早开发的autocomplete(代码自动补全)体验,就是Windsurf里的第一个产品。当时在打磨产品体验方面的进度其实拖慢了。而之所以体验不够好,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当时被绑定在VS Code里,它的UI扩展能力比较有限,导致没法实现更好的交互逻辑。
但后来开发了Windsurf,拥有了自己的编辑器后,就能在用户体验上投入得更多,最终也实现了真正想要的效果。
Harry:你刚刚提到VS Code,那让我想到一个话题——护城河(moat, 即企业在市场中的结构性竞争优势)和产品防御力。你觉得在AI的世界里,护城河是不是已经“死了”?大家经常说Cursor和Windsurf可以随时切换,我今天用你,明天换对方也没问题。那你怎么看?护城河真的不存在了吗?
Varun:对于初创公司来说,护城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有点“虚”。如果你读过《七种力量》(Seven Powers)这本书,里面有很多关于护城河的精彩理论。
Harry:我很喜欢那本书。
Varun:我也觉得它很好,但对于初创公司来说,那套理论很多时候还是太早了。比如说,就算你公司里有50个顶级工程师,全是最优秀的人才。团队已经非常强,大多数工程师来自MIT,甚至是MIT最顶尖的那一批。可即使如此,加起来你也只是拥有“数百工程人年”的产品积累。而在我们的领域里,其他人也完全可以从头搭建出类似的东西。
所以在这个赛道上,唯一真正的护城河就是——速度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:你需要比别人更早知道“哪里有坑”,需要通过快速的学习,积累出持续性的优势。我常举的例子是NVIDIA。外界总觉得他们的护城河是CUDA,但我并不这么看。大型公司,比如 OpenAI、Anthropic、Google,他们自己都在造TPU、花几十亿美元投入芯片。你觉得如果CUDA不存在,他们就不用NVIDIA的GPU吗?当然会,他们可以直接写assembly,写底层汇编也会照样跑在NVIDIA的硬件上。因为这东西太值钱了,没得选。
人们选择NVIDIA,不是因为它的锁定机制,而是因为它真的做得好。它的低精度浮点运算能力非常强,芯片之间的interconnect也很强,整体运算速度快。而且它每年都有“倒计时炸弹”压在头上——如果下一代硬件在速度、内存带宽上跟不上,那它就会被AMD追上。你看,这种机制跟Google这种平台型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但NVIDIA依然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之一。
Harry:我完全同意,尤其是在初创公司阶段,护城河确实比较虚。但如果你想象一下,有两家公司今天同时出发,其中一家公司被整合进一个巨头,比如OpenAI 或Anthropic,它们立刻就拥有了分发能力、品牌认知,还有能以超大规模购买芯片的资源。这种情况下,《七种力量》那一套理论是不是就又变得重要了?护城河又存在了?
Varun:,那种观点之所以没那么成立,是因为即便在那种情况下,“速度”仍然非常关键。你可以问问自己:为什么一家初创公司会在一个重要赛道里击败巨头?为什么2000年代初是Google赢了,而当时Microsoft明明已经是巨无霸了?归根到底,是因为这家公司有更深刻的洞察,而且能在战略执行上压倒对手。
Harry:但你不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,分发比速度还重要吗?你可能做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,速度也很快,但如果 Anthropic 明天把Cursor捆绑进Claude,然后直接推送给所有企业客户,那你就完了。他们有渠道、有品牌、有覆盖率。
Varun:你说得没错,这是非常现实的压力。但这也是我们创业这么长时间学到的东西——你必须做出“无法忽视”的产品。如果你的产品只是“比别人好一点”,那确实会被碾压。但如果它好到让用户愿意绕过默认选项、专门来找你,那你就有生存空间。
我们现在的用户就是这样。我们并不是通过市场投放吸引他们的,甚至很多用户一开始连Windsurf是谁都不知道。他们只是试了一下我们的产品,然后发现它真的有巨大不同。这种“巨大不同”,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竞争力。你问我要怎么描述Windsurf的目标,我会说,我们要做的是一个“比默认好两个数量级”的开发体验。
Harry:那你怎么评估产品到底有没有达到那个“两个数量级的差距”?你怎么看一个产品有没有到那个“跳跃点”(escape velocity)?
Varun:有一个最直观的信号是——用户自己会带来新用户。我们内部有一个“单用户指标”(single user metric),就是看一个人用完产品之后,有没有回头、有没有带来别人、有没有开始把产品集成进他自己的工作流程里。
这和传统的“团队销售型”指标不一样。很多AI产品的商业模式,其实还处在SaaS旧逻辑里,就是靠团队决策、预算分配、上层推动。而Windsurf不是。我们看到的是,用户用完之后自己来找我们说:“我能不能自己买?”、“我能不能给我整个团队部署一下?”这种从个体主动扩散出来的增长信号,是我目前最看重的。
AI未来与竞争壁垒:长远规划
Harry:你觉得在code AI这个领域里,有什么是大公司短期内做不到的?有哪些是留给像Windsurf这样的团队的机会?
Varun:最大的机会,在于我们能去构建那些需要非常高密度工程直觉的东西。
大公司可能会说:“我们有400个产品经理,可以把每个功能都评审一遍。”但开发者工具不一样,真正的壁垒往往不在某个具体功能,而是在连续一整天、整个工作流中的体验。你是不是懂得什么时候该弹出窗口、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、什么时候自动补全要aggressive、什么时候又要保守一点,这些东西没有明确规则。这种“流动中的精度感”,其实只有做过一线开发、并且对用户有高度同理心的团队,才有可能做得出来。而大公司,由于组织结构的限制,往往很难在这方面做到极致。
Harry:你觉得所有做code AI的公司,最后都会变成一个IDE吗?也就是说,不管你现在是做Agent、自动补全,还是语言服务器协议,大家最终都会变成一个完整的IDE?
Varun:是的,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。这就像是你在说:“我有个方法可以预测接下来每句话会怎么写”,然后你却告诉我你不想去做编辑器——这就说不通。如果你有能力建模所有的上下文,知道用户接下来可能要写什么,甚至还知道用户修改代码的意图,你却不去控制 UI,那你就无法真正释放这些能力的价值。用户要的是整个“写代码”的过程能够高效、流畅、有反馈感。你如果只控制其中一环,体验一定是割裂的。
Harry:那对于用户来说,是不是也意味着——他们今后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写代码,这个平台是以AI为中心构建的?
Varun:是的。长期来看,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开发环境。团队里很多人以前做过自动驾驶,而自动驾驶的技术曲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——我们一直以为自动驾驶是一个“感知”问题,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“接口”问题。
同样的道理,代码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转变,也是“接口”的改变。现在的开发接口还是以手写文本为核心的,而AI开发的理想形态,应该是更高层的表达方式,比如自然语言、流程图,甚至是功能目标。而Agent、token、context 这些能力的发展,意味着IDE这个边界正在被打破。你并不需要再靠传统IDE的形式去组织代码。开发者所期望的,是和代码之间更高效、更智能的交互接口。
Harry:你们最后是变成一个IDE本身,还是说你们只是变成IDE的“AI 层”?毕竟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,提供一种“嵌入式AI层”,比如通过扩展接口接入现有编辑器。
Varun:这是个好问题,我也不觉得答案是非黑即白。更准确的说法是:我们希望成为开发环境中的AI核心。不管最终的UI是什么样的,不管用户是喜欢我们自己的编辑器,还是希望把它嵌入VS Code、JetBrains或其他地方,我们真正要构建的是智能层本身——也就是具备Agent能力的系统,它能理解代码库、上下文和用户意图。
我们其实已经开放了Windsurf的API,很多用户就是把Windsurf嵌入到他们自己写的定制开发工具里使用的。换句话说,IDE只是UI层,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理解层和行动层。这两个才是决定AI工具价值的核心。
Harry:从另一个角度看,用户为什么愿意用你们的工具?毕竟每个人都可以调一个开源模型,加点prompt,写个AgentLoop,搭个前端。你怎么说服他们用Windsurf,而不是自己造轮子?
Varun:这个问题我想分三个层次来回答。
第一,数据层。我们对代码的理解是深度结构化的,不只是把代码作为token去处理。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语法解析器、上下文建模系统,这些都是开箱即用的东西,不是靠prompt可以解决的。
第二,反馈循环。我们做了很多智能微调的机制,Agent不会简单重复“用户问—模型答—用户问”的回合式结构,而是能主动评估自己的行为,调整策略。这背后用到了复杂的状态追踪与控制逻辑。
第三,工程能力与体验设计。一个真正好用的开发工具,不是堆积功能,而是把所有能力组织得刚刚好。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去打磨这个体验边界,比如什么时候让Agent安静,什么时候该“打断”用户;什么时候自动弹出对话框,什么时候保持无声运行。
这些东西不是靠堆API能实现的,它需要你既懂技术,又真的在乎开发者的工作流。
Harry:你怎么看AI产品的“人机边界”?就是说,到底哪些事该让Agent全自动完成,哪些又是该保留给人的决策权?
Varun:这个问题特别重要。我们现在设计Agent时,就非常关注这一点。比如,让Agent在用户写代码的时候自动分析上下文,但不会立刻执行操作,除非它有非常高的信心,并且能明确解释它的行为理由。而当用户进入更高层次的任务,比如调试逻辑、重构架构,我们的Agent就会退到辅助位置,提出建议、提示上下文,但不主动干预。
你可以理解为,Agent是在不断地问自己:“我现在该不该出手?”这种判断力,其实比模型本身的输出质量更难构建,但也更有价值。
Harry:这是我最近录过的最喜欢的一期节目之一了。太棒了。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来聊这些。
Varun:非常感谢你邀请我。这次聊得真的特别开心。
Harry: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,你跟我说,“老实说,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。”但现在你们已经构建出了Windsurf,一个非常酷、影响深远的产品。能够见证这个过程真的太棒了。
Varun:是的,那时候真的还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(笑)。而且这一点也没什么可丢人的。说实话,很多人创业时都太想“证明自己是对的”,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找到真正对的方向,而不是坚持最初的想法。你得不断观察市场,不断问自己:“我们是否还在解决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?”如果不是,那就要立刻转向。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。
Harry: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信念。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说的那句话:初创公司成功不是因为把很多事做对了,而是因为把那一件事做得非常好。希望听众们也能记住这一点。
Varun:谢谢你。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这一点,尤其是在产品开始扩展之后更是如此。你越早抓住那个关键方向,就越能集中火力做出突破。
Harry:那下次再聊的时候,就来看看Windsurf能不能把这一件事继续做成10倍,甚至100倍的效果吧。
Varun:我们会努力的!
编译:Mia Pan